番屯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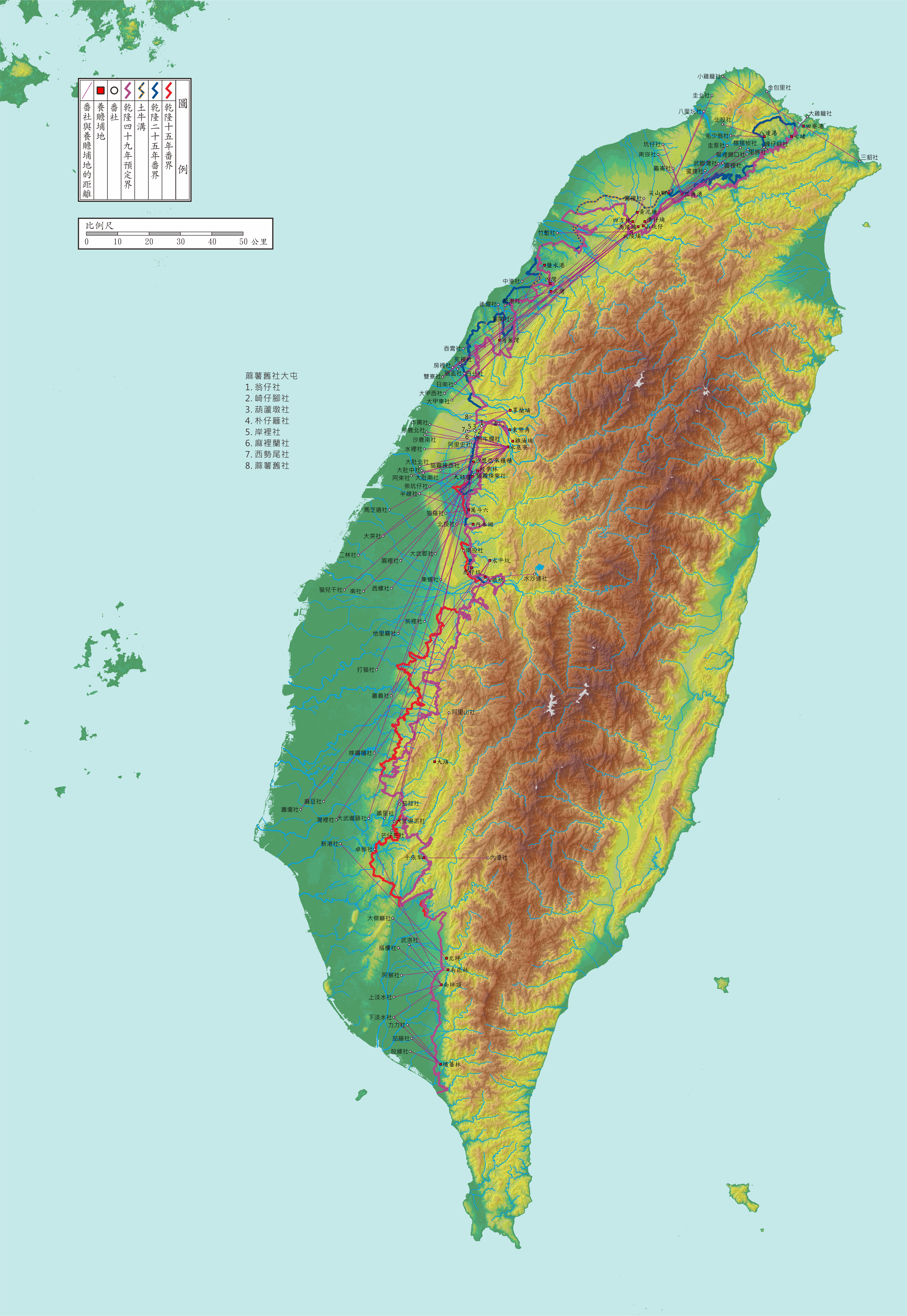
【圖1】乾隆台灣番界及屯番養贍埔地配置圖。(柯志明提供)
設屯與分撥屯地
1790年(乾隆55年)12月軍機大臣與兵部等部議奏閩浙總督伍拉納奏准設屯與分撥屯地案內,伍拉納所附勘丈委員徐夢麟等的稟文,說明了先後紅、藍、紫、綠線邊界的沿革與本次的處理方式:
臺陽近山地廣,民多越墾,往往深入內地,生端滋事。雖曾於乾隆十五年、二十五年兩次立碑,併於淡、彰二處挑築溝土,以分界限,但日久漸廢,旋遭匪亂〔按:林爽文事件〕,其未築者固屬空談,其已築者亦為頹毀。……應請以此次清查屯地,歸屯為界。……從前以紅、藍、紫色畫線為界,今則添繪綠線,以別新舊。(臺案彙錄甲集:46)
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與「歸屯為界」
歷次議奏及劃定邊界的具體過程簡要陳述如下(請參見「乾隆臺灣番界及屯番養贍埔地配置圖」內重繪於現代地圖上的歷次邊界):福建布政使高山1745年(乾隆9年)1月20日〈臺郡民番現在應行應禁事宜〉奏內「劃清界限,使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之議,隔年經高宗發交部議覆准,是為清代台灣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之濫觴。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於1750年(乾隆15年)立碑定界的邊界稱為紅線。基本上,紅線界如高山原奏內所建議的,是沿襲康熙、雍正時的舊界僅略做調整。卸任臺灣知府鍾德1757年(乾隆22年)初勘,閩浙總督楊應琚1758年(乾隆23年)奏准「挑挖深溝、堆築土牛」,委由總兵馬龍圖、臺灣道楊景素於年底覆勘,繼任閩浙總督楊廷璋1760年(乾隆25年)再加調整後奏報確立的「新界」是為藍線。藍線界在1751年(乾隆26年)楊景素完成挑溝築牛的工程後,又稱土牛界。1784年(乾隆49年)閩浙總督富勒渾奏准由卸任臺灣道楊廷樺主持勘查、繪圖造冊詳報但未定案的界線繪為紫線。林爽文事件後,欽差大臣征臺統帥福康安、福建巡撫徐嗣曾1788年(乾隆53年)奏准、專委留辦臺灣事務之泉州知府徐夢麟等於1790年(乾隆55年)釐定以屯地外緣為準的邊界則繪為綠線,這也是最後一條確定的邊界。由於該次清查界外田園埔地的目的主要在設立番屯制並確保其口糧來源,故稱「清查屯地」。土牛界外已墾田園、未墾埔地在清查並確定歸屬之後,新的邊界就依之劃定,又稱「歸屯為界」。
相較而言,1790年(乾隆55年)「歸屯為界」的綠線界,在硬體工程規模上又退回藍線界以前立碑(以點而非線)定界的層次,但該次劃界真正重要的意義在設立番屯制,以及相關土地歸屬和租佃關係的重大制度變革,堪以作為與藍線界並立的替代性方案。福康安等奏准設立番屯制,熟番人力的角色從勞役提供者轉換為補助性的戰略武力,朝廷中央在政策上相應豁免其承應徭役的部分。
「弄兵之漸」與番屯制
清高宗對林爽文事件「弄兵之漸」的反省促成邊界與界外埔地治理政策變革的契機。征討林爽文的清軍統帥福康安等曾上奏提及乾隆年間幾次清界的時間與原委:
臺灣東界內山本多曠土,乾隆十五年暨二十三年〔按:係指楊應琚乾隆二十三年勘界事,非乾隆二十五年楊廷璋調整確定藍線界事〕節經勘定界址,奏請禁民越墾,准令熟番等打牲耕種,以資生計。無如游民聚處日多,越界佃耕,漸成熟業;以致爭奪滋事,控案甚多。前經富勒渾奏明,專委鎮、道確切勘丈,尚未勘明詳報,即值逆匪(林爽文)滋事。(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68輯:86)
利用多元族群襄助統治
由於林爽文的叛亂,1784年(乾隆49年)清查迄未定案的界外土地政策發生巨大的變化。林爽文事件暴露了許多台灣既存的結構性問題,高宗認識到其嚴重性,特別指示福建巡撫徐嗣曾渡台,輔佐福康安徹底整頓及規劃善後事宜。福、徐二人的善後改革裡,最重要也最困難的部分,仍然是在如何妥善規劃土牛界外田園埔地的歸屬與租佃安排,以利用台灣多元族群的現象來襄助清廷的台灣統治。
1788年(乾隆53年)4月9日,高宗就前此陸續指示的各項台灣善後應辦事宜後再加上一條:有鑑於「此次搜捕逆匪,該處熟番尚為得力」,要福康安與徐嗣曾挑募熟番入伍。福、徐二人遂效法四川屯練降番之例,擬定〈熟番募補屯丁章程〉,於5月31日上奏,奉旨交軍機大臣與兵部等部議覆,7月20日奉准施行。章程內除挑募熟番屯丁及番屯組織的細則外,主要的內容在於規劃如何清查及處理土牛界外的土地,以撥充屯番糧餉。續後即根據該章程所立下的原則而執行土地清查與裁定土牛界外的地權歸屬。
番隘制改成番屯制
改革裡最重要的變化是清廷擴大利用熟番武力,將原有的番隘制改成番屯制:挑選隨同征剿林爽文叛亂的熟番壯丁4,000名,作為配合正規軍維護治安與守邊的「民兵團」;同時,因應供給屯番軍餉的需求,就界外田園埔地重新規劃用途。這項結合招募屯番與界外田土重規劃的初步計畫成形於前述福康安、徐嗣曾(實際規劃者應為徐)的〈熟番募補屯丁章程〉裡。照福、徐二人奏准「將熟番挑募屯丁,酌撥近山未墾埔地,以資養贍」之原議,撥交屯番自耕或(與居住地相距過遠時)招佃開墾的未墾荒埔,稱為養贍埔地(各社養贍埔地所在參見「乾隆臺灣番界及屯番養贍埔地配置圖」)。徐嗣曾1788年(乾隆53年)12月的奏文內稱:「查該番等有埔地五千餘甲,田面、田底俱歸承種〔底線筆者所加〕,每一名受田一甲,可得穀三、四十石」,點明養贍埔地原係撥給屯番自出工本、開墾耕作,墾成後擁有田底,且因上無墾戶,此田底業實一併含田面業在內。撥給的屯地距離太遠,屯番不方便自己開墾的話,也可以招漢佃戶開墾,「近者給地自種,遠者招佃承耕」,「分租〔按:招佃分租〕、分地〔按:分地自種〕,相輔而行」。不過,由於招佃開墾不是「自出工本」,並未兼有田底業,只能抽收田面租(又稱大租)。養贍埔地墾成後與番社田園一例免稅,不得典賣漢人。但其與一般番社田園仍有差別:該屯丁離職出缺時只能由被挑補為屯丁的子弟遞補,不得私自轉讓給其他熟番。
從兵農合一到建立專屬熟番管業收租的中間地帶
徐夢麟等原曾建議將養贍埔地全面招佃,委託佃首代為經營收租。徐嗣曾予以否決,除繼續堅持屯田制「必須撥地分耕」外,對不得已而需招佃開墾的養贍埔地,要求「官為經營」,以杜「侵漁」,「一切租銀、餉銀,仍宜地方官主其收放,屯官經其支領」,並估計每月各屯丁約可配發餉銀二兩。然而,徐夢麟等在執行上似乎有所困難,並未能將適用於丈溢歸屯田園的「官為經理」原則延伸至養贍埔地。而且,他也沒有交代養贍埔地「分地」(分地自耕)、「分租」(抽分大租)的原則與實際執行情形如何,僅只含混地聲稱,由於「抽分大租歲入無幾」,不少屯番及其弟男子姪「情願抽撥往耕」。
撥歸屯番的養贍埔地雖然規定要自行墾種,卻也不排除在「路遠」(或假借此理由)的情形下,變通准許招漢佃戶代墾。土牛界至新界間(綠藍線間)的田園埔地既無法保留給熟番自耕,也沒有禁止漢人移入此地帶佃耕乃至以業戶身分持有土地,清廷顯然已經無意追求一個純屬熟番族群的夾心層地帶,甚至連退而求其次,建立一個專屬熟番管業收租的中間地帶(即新舊界間作為夾心層後勤地帶),也無法堅持。
番屯制雖高倡兵農合一的理想,意圖在綠藍線間的養贍埔地扶植屯丁自耕,卻始終無法落實。清廷充其量不過是為了維持一支4,000人的熟番民兵武力,在新舊界間(透過匿報田園歸屯充餉及確保養贍埔地於漢佃墾成後供納地租)勉力幫屯番找尋及維護其地租收入而已。雖然繼續使用分而治之的統治技藝分化族群,番屯制下的邊境體制,在外表上仍維持三層,但核心地帶夾心層的部署原則已然更易,稱不上是高山原初規劃的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了。
參考文獻:-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甲集》,臺灣文獻叢刊第31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
- 陳壽祺編,《福建通志臺灣府》(1871,同治10年),臺灣文獻叢刊第84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高宗實錄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186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1-75輯,故宮複印本,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年。